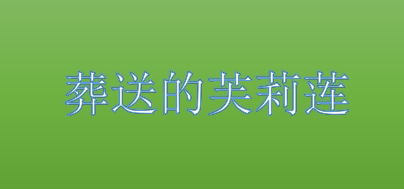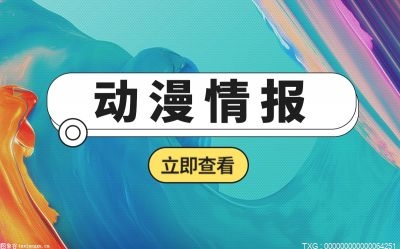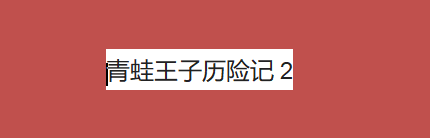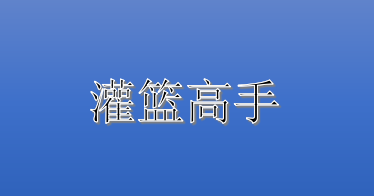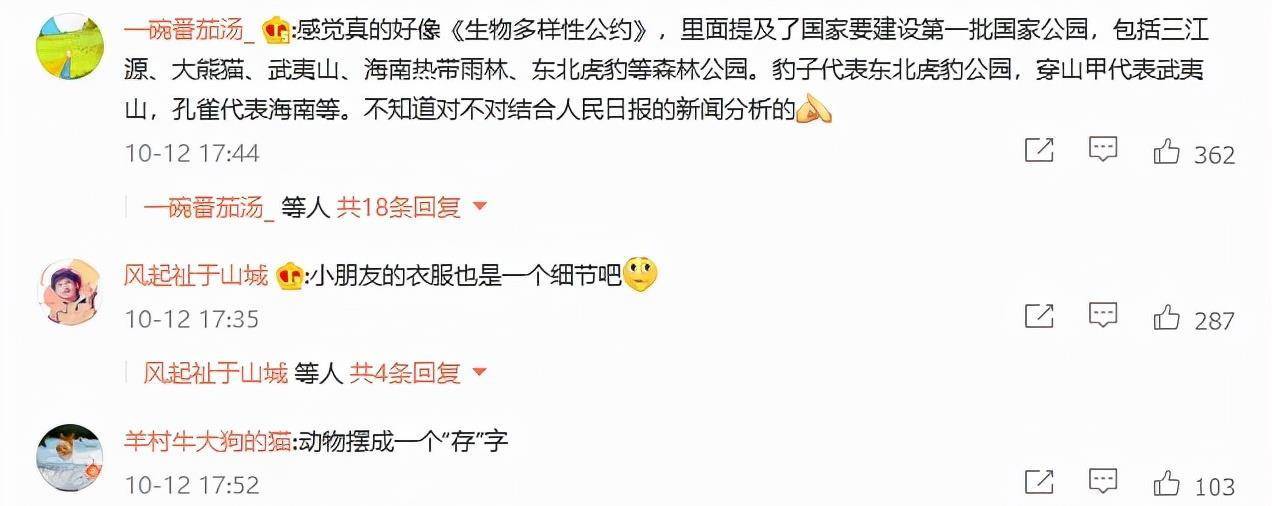在哲学和小说里,经常出现关于“名字”意义的探讨,我们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又如何知道名字从何而来?
“名字”通常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的意义,变成一种可以操控、创造甚至改变意志的力量,而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便是对“名字”的一次全新诠释。
宫崎骏曾经说:“夺走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会改变别人称呼他的方式,更是一种完全控制他人的方法。”{1}
 【资料图】
【资料图】
这正是《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的哲学理念,她夺走了千寻的本名,而赋予了主角“千”的名字。
汤婆婆(右)
这也是很多宗教习俗中的基本概念,在幻想作品和民间传说中也是如此。
例如厄休拉·勒古恩的地海系列小说中名字是魔法和力量的核心,其中写道:巫师唯有掌握其真名才能操纵人或物。
还有德国民间故事“侏儒怪”,日本传说“木匠和鬼六”,后者是一问一答猜测名字的故事。
正如罗朗·巴特所说:“我知晓名字的东西不能真正刺激到我,说不出名字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慌乱征兆。”{2}
这种力量的体现,像《哈利·波特》中用“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或者“汤姆·里德尔”来代指伏地魔。
所以,无论这种力量是控制、创造,还是毁灭,如果你是幻想故事中的角色,名字可能会非常重要。
在西方国家有着已婚女子冠夫姓的习俗,这总是离不开所有权的历史,即便当代人的思想已经改变。而在日本,《民法典》里还有着“夫妻双方必须同姓”的规定。
正是关于名字和身份的基本问题,主导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诸多哲学思想。
千寻:千寻,那是我的名字吧,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忘了我的名字,她差点儿就把它从我这里夺走了。白龙:如果你完全忘记了,就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回想我的名字。(《千与千寻》)
影片在这里暗示人的名字是自我的缩写,所以能够代表自我。
而现实却如《千与千寻》中汤婆婆般道出:真是个漂亮名字,现在属于我了。
这个比较,似乎也引发出像“千”与“千寻”之间的身份危机,使得名字的力量成为想象中、无实体的,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脚,更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但却显得真实可知。
千寻将要搬去新的地方,有新的家和学校。这类似于皮克斯的《头脑特工队》的故事前情,离开成长的环境就仿佛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腐蚀。
但宫崎骏让这种感觉从失去童年家园扩大到国家的规模,利用文化身份的语境去探索个人或个人的一部分,国家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并列。
宫崎骏解释说:“在这个无边界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或忘记了过去的人,将只能就像一缕微光般消失。”{4}
这与作家苏珊·纳皮尔的解释相呼应。
“《千与千寻》的叙事轨迹围绕着日本人的文化认同与异质之间的对立展开,并且至少是含蓄的质疑了日本国民性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生存能力。”苏珊·纳皮尔{5}
在国家身份这一话题上,意识流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922年的小说《尤利西斯》“独眼巨人”一章中有一段重要的对话。
主角利奥波德·布鲁姆既是爱尔兰人又是犹太人,且难以调和这两种身份,他说:国家就是同一地方住着同样的人们。
作家卡尔文·奈特总结《尤利西斯》里的国家性说:“詹姆斯·乔伊斯没有追求表面上的全面性,而是证明了一个国家是无法被代表的。”{6}
这种重压在《千与千寻》中的反应是传统的日本性和消费主义现代性的并称,还有西方文化的同质化,这个故事同时显示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家和归属感的重要性。
对于无脸男和白龙“家”的缺失破坏了自我身份。无脸男似乎是如同浮萍般游荡着,试图消磨自我。而白龙的家“琥珀川”早已不复存在,他的真名作为身份的一部分已经被重塑。
纳皮尔还评价《千与千寻》道:“它意味着边界的普遍渗透性,唤起一个无界的世界,充满着失去、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的身份,以及被遗弃的幻影。在这里,古老的真理和模式似乎不再有效,回家的深切愿望永远无法实现。”{7}
或许这可归结到文化变革上,正因如此,一个老龄化国家拼命抓住正在消散的过去,错误的试图将文化连同他们自身翻新重建。
电影中对个人和文化身份的探讨交织在一起,用文化认同的主题来加强千寻的自我发现之旅,就像《尤利西斯》“独眼巨人”章中用第一人称叙事“我”,而在其他章节中没有这种用法。
《尤利西斯》每一章的主题和意象都源自于荷马的《奥德赛》,在“独眼巨人”章,奥德修斯登上独眼巨人之岛,虽然这可能是想体现叙事者的视点有限,但“我”反映的是一种狭隘的身份观点。
实际上,若是质疑一番,原本确定的“我”可能渐渐变得模糊,就好像定义一个国家会崩溃于国家自身的重压,对自我的定义也同样艰难。
这一章的叙事者一直没有名字,将不可更改的“我”和读者质疑的“谁”相对比,就像独眼巨人在质疑奥德修斯一样。
奥德修斯在拉丁文中为尤利西斯,这本小说正得名于此,奥德修斯告诉独眼巨人,他名为Nobody
成为失去名字的Nobody,进而产生对失去自我的恐惧,是《千与千寻》里关于名字的中心问题。
回到成长这一概念上,电影也认同改变是必须的,是有意义的,以及自我不仅是外界赋予的身份和名字,也是自己所做的抉择。
千寻的旅程一定程度上重获独立。独立性的缺失在片头搬家的段落中可见一斑,在汤婆婆的合约中更进一步。被删除的名字反映出她的遗弃感和迷失感,于是“千寻”成为了“千”。
在双重身份这一主题上,虽然“千”这个名字对于千寻是不公平的,但它引入了名字和身份并不是严格固定的这一概念。
没有哪一个动画的角色是一座孤岛,千寻对身份的探索起源于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寻找自我的位置,将自己置于文化和历史背景中。
后来,千寻的目标不再是寻找自己失去的部分。自那以后,回家的愿望永远不会实现,就像我们知道火车只往单向行进,取而代之的是夺回控制,同时成长为一个更大的群体中的一部分,在即将崩塌的世界中,选择自己的身份。
《千与千寻》所暗示的是认识你自己要经历反复的评估,因为自我处在不断变化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积极行动,可能会讨厌后来的自己。
千寻确实找回了名字,但她没有变回过去的自己,那个“自己”属于过去、老家、旧友,就像那些属于日本的传统。
千寻害怕在远离过往生活的同时失去自己,反应出一种日本全国性的恐惧,或者说至少是宫崎骏对丢失传统的恐惧。
我们不知道千寻从何处而来,又去向何方,只看到两者之间,因为这个“之间”就是故事的一切,虽然这可能意味着她将永远回不了家,但宫崎骏告诉我们至少可以控制现在的自己。
●参考资料:{1}、{4}宫崎骏,《千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电影的目的》,2001年;{2}罗朗·巴特,;{3}艾莉森·卡茨,ATPdiary,2016年;{5}、{7}苏珊·纳皮尔,,2006年;{6}卡尔文·奈特,,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