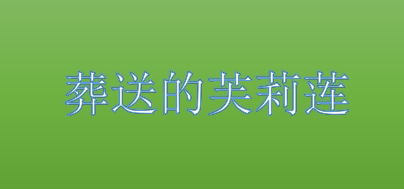在阅读小哥前,辛苦您点下“关注”,方便您讨论转发。作者定会不负众望,持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文|冯蜜的柚子茶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编辑|冯蜜的柚子茶
一、1980年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与阶级话语建构
这部木偶剧版电影是新我们成立后少数民族题材的经典动画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时尚。影片主人公名为阿凡提,实际上,阿凡提只是维吾尔族智慧、勇敢和睿智的鲜明形象代表,并非真有其人,这一形象也不止一次出现在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中。
这部木偶剧集中反映了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文化背景下劳动网民勤劳、勇敢的主流精神,与巴依老爷这一符码化的贪婪、剥削的地主形象形成了阶级性的对立与对比。所以,对于这部木偶剧版的电影的阶级话语的探讨,首先要去“追根溯源”影视作品的时代创作语境。
(一)《阿凡提的故事》的创作语境
木偶剧《阿凡提的故事》拍摄完成于1979年,发行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随着艺术创作新时期的到来和改革时尚进程的推进,我们电影的创作逐步从“恢复时期”暴露出的问题走向了一个新的创作语境。恢复时期的影视作品不少是在新时期以前就投入拍摄的,所以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阶级斗争的模式,“三突出”痕迹尚未淡化。
新的创作语境在电影史上的公认日期就是起于1979年,1979年是转折的一年,是开始创新的一年。改革时尚带来的思想解放加快了文艺创作思想的解放,电影逐步从政治宣传的工具中摆脱出来。艺术家通过电影创作可以充分发挥个性化的风格,强化个体对于生活的理解。
从1979年到1980年,电影开始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技巧进行了大改革式的创新,因此亦被称为“形式美学”追求。这时期的影视作品已经开始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观念,但现实主义的表达仍不够深度和多元,只是停留在对于美好事物的表现。
直到1981年之后才开始对电影中的“湖南美学”有了新的认知和发展,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塑造人物没有深入地去挖掘内在情感,只是拘泥于外在形式,这点未能完全摆脱“十七年”电影创作的模式。
比如《生活的颤音》讲述男女主人公美好爱情时就没有着力描写,更没有谈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波折。第三个创作特征是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善与恶对立的阶级观问题,亦即阶级叙事的存在。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在这种创作语境中诞生,也必然存在着这三方面特征的痕迹,尤其是阶级话语的叙事建构。
(二)木偶剧的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
木偶剧《阿凡提的故事》中的阿凡提形象典型、具有突出的个性,且传奇色彩围绕其身。为了塑造阿凡提的形象,摄制组两次前往新疆,最终产生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形象:头戴一顶民族花帽,留着山羊胡须,双手拿着弹拨乐器,背朝前脸朝后地骑着一头小毛驴。
这样的形象早已深深植根于80后和90后观众的心中。但由于存在传奇性的英雄主义色彩,阿凡提的形象显得有些孤立,虽然也与当地民众说话交流,打趣玩笑,但与老百姓还是保持着一种智者和领导范的“间离感”,气场很强,说话办事性格沉稳。阿凡提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在其故事中反映得淋漓尽致,表达了自己对人生权利得失问题的深入思考。
在当时的艺术创作语境下,影视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内心情感戏不足,这部木偶剧既没有深入刻画阿凡提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也没有涉及纯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简俗易懂。木偶剧在这方面比较契合民间故事中所设定的人物原型。
阿凡提疾恶如仇、幽默风趣、睿智聪慧又极富正义感,为穷人打抱不平,让一切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恶人”都受到了出其不意、啼笑皆非的处罚和报应。从作品整体风格来看,现实生活的反映生动不做作,木偶剧中展现了浓厚的维吾尔族特色化的风土人情,各种服装饰品、场景设计和道具设计基本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除了美工场景设计,还有朗朗上口的维吾尔族歌谣传唱至今———《人人都叫我阿凡提》,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本身的现实倾向。如果深入剖析,木偶剧在表现现实时不够多元化,除了揭露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主阶级的贪财等劣迹,缺乏对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阴暗面的暴露,但是这部动画剧的受众定位只是青少年群体,没必要过度苛责。
(三)历史语境的正义话语———阶级叙事
我们的阶级叙事大约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流派,在电影界则逐渐影响到了左翼电影运动。近代以来,贫苦大众被我们的官僚和封建主义阶级压迫并被逼向了生存的绝境,他们不得不进行革命式的抗战,才能“翻身农奴把歌唱”,可以说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工农的解放。
文学和电影作为宣教工具,必须谈阶级话语,把革命斗争的伟大精神用文字和荧幕语言记录下来,谱写进历史。总之,艺术创作者通过阶级叙事话语的精心塑造,表达工农群体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表述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革命精神的主观理解和信任认同。
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主要从形象设定、叙事安排以及价值评判三方面呈现了“阶级叙事”。从人物形象来说,主人公阿凡提用自己的智慧为穷人打抱不平,让丑恶阶级得到了报应和惩罚。
这些丑恶阶级往往是昏庸愚昧的国王及官员、以巴依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还包括市井的无赖泼皮等,而善的一方往往是维吾尔族普通劳动网民。木偶剧的“善”与“恶”鲜明对立,两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结局都是善的一方获胜。
形象的设定计划了叙事的安排,这种叙事表达主要就是强调“弱者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的结局,所以通常不强调结构技巧,而是通过自然流畅的剪辑来叙述剧情,表现对立与冲突。这正如好莱坞式电影———国外好莱坞早期的类型电影就提倡建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阶级观以褒扬秩序的建立以及人性的美好。
对于价值评判和导向,阶级叙事主要强调了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木偶剧中,维吾尔族老百姓构建了以本阶级利益为共同体的新的社会生存道德联系,与官僚和地主阶级形成对抗,若没有这种团结,力量渺小便不足以制胜。
张天翼在他的小说《仇恨》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表现了背井离乡的难民在逃亡的路上“要活一块活,要伤一块伤”的阶级感情,他们发疯似的攻击三个溃逃的士兵,很气愤地要吃他们的肉,但当明白了这些士兵也是种田人,即与他们“都一样是受害者”的时候,他们才懂得了不应该去仇恨这些“兵”,而是应该仇恨军阀“大帅”。
在木偶剧中,以《卖树荫》为例,主人公阿凡提花钱出了买树荫的主意,但若没有维吾尔族老百姓团结起来去“整弄”地主巴依老爷,巴依老爷也不会做出妥协和让步,这就是阶级群体的力量。
(四)评价与思考:《阿凡提的故事》的“好莱坞西部片式”元素
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是在当时文艺创作刚刚获得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产出不只是满足青少年群体的娱乐消遣,同时也具有较高层次的符号化意义。这个意义宏观上可以媲美经典好莱坞西部片之于国外的文化意义。
好莱坞西部片也是讲阶级叙事的,这里的阶级是“国外的阶级”———国外蛮荒与文明的碰撞。同为西部题材(新疆属我们西部)作品,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在三方面体现了好莱坞西部片式的元素:其一就是阶级的冲突与对立,上文已经重点详述。
其二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西部片大量展示了西部特色的生活细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如《荒漠三雄》中就有三个悍匪为救下一个婴儿成为三个教父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样的情节,而《阿凡提的故事》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向真主祈求和宣誓”这样的宗教式片段。
其三是讲求趣味性。多数好莱坞西部片都是走的轻喜剧的风格,而这部木偶剧全篇都是走的“幽默诙谐”的路子。总之,好莱坞西部电影兼顾性表达了电影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信仰与娱乐消遣三者并存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文化。讲述“阶级叙事”的这部木偶剧也同样展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娱乐消遣以及民族元素的融合,意义非凡,值得深入研究。
二、动画电影版《阿凡提之奇幻历险》的情感话语策略
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产出30多年,堪称80后、90后群体的童年经典。30多年之后的2018年,终于又出品上映了一部“阿凡提”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幻历险》。但从这部电影诞生的历史语境来看,与之前的木偶剧版电影《阿凡提的故事》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较大的变化。
(一)传统阶级叙事的“失落”
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化”这一社会语境关键词的诞生使得我们社会和文化大踏步全面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涉及了政治、经济、法律、人文艺术等方方面面。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直到21世纪的今天,大批量的优秀国产电影先后走出去门,在国际上获得了各种电影节奖项,可以说,我们之电影产业在全球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比例不低。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产电影作品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也在积极地开始应对挑战和自觉转型,我们导演在新的发展语境下开始放开手脚,自由创作,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电影产业接轨。
其实,好莱坞影业发展至今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他们不断吸纳欧洲艺术电影的创作经验,在表现手法上突出了电影的影像功能,重点是打破了二元阶级对立的叙事结构,“定型化”的人物形象不再出现,而是根据其性格自身的发展展现其自然本性,“善”与“恶”不再是划分人物好坏之泾渭分明的标准,这标志着传统的阶级叙事已经走向了失落。
新语境下的我们电影在国际市场上主题更趋于多元化和多样化,更偏重于展现人性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逐渐淡化二元对立的阶级观,着重表达人物内心情感和细节描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阶级叙事“失落”以后。
电影创作只是不再搞阶级分野和人物对立,并不意味着是要放弃大众和放弃对于大众主体历史语境的建构,而是更加契合了新时代的大众文化语境,因为在新时期,好的商业电影是能通过娱乐来实现大众精神上的疏导,观众和市场的认同是实现创作者艺术观念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