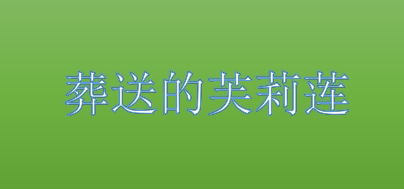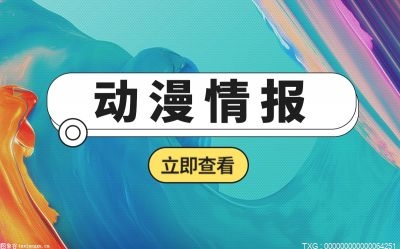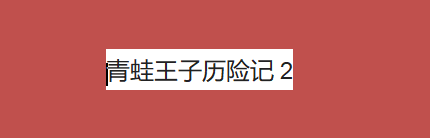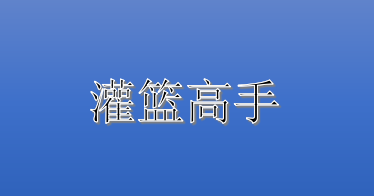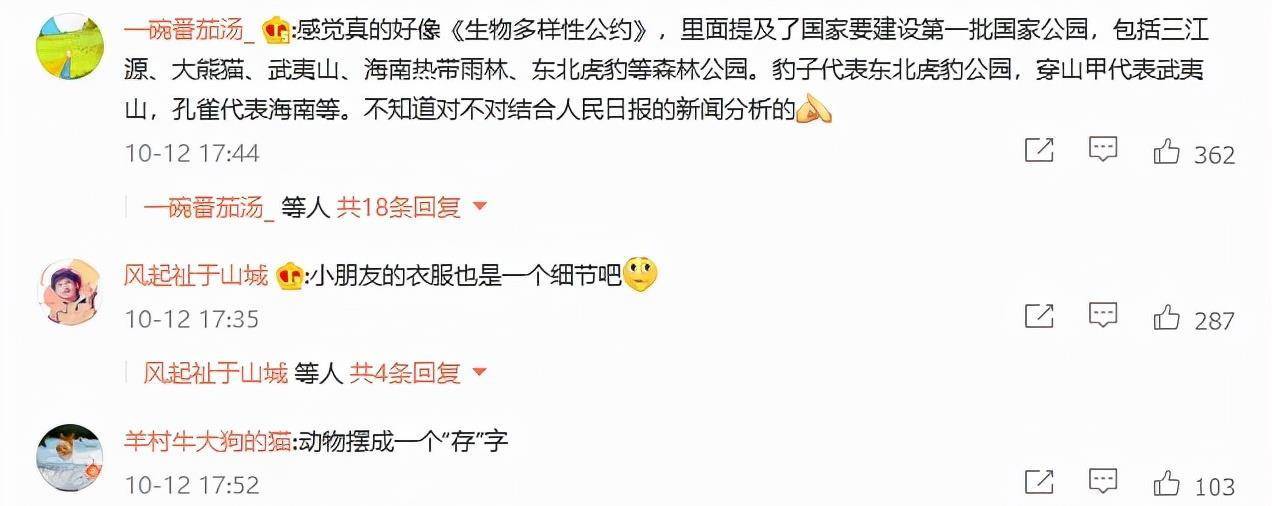我想观众会这样形容英格玛·伯格曼的《假面》,它焦躁不安,如梦似幻,又极具表演性。
《假面》中的主角艾玛(左)和伊丽莎白(右)
 (资料图)
(资料图)
这部作品中探索了几个深奥的主题,如什么定义了我们?什么造就了如今的我们?
英格玛·伯格曼(拍摄于1960年)
英格玛·伯格曼的哲学要义是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正确的影像应该是通往心灵力量的一扇门,塑造我们独特的想象。
引用英格玛·伯格曼自己的话说:“没有艺术能像电影一样进入我们的良知,直接触动我们的情感,潜入我们灵魂的深处。”
正是他对影像表达的重视度,加上《假面》简单的预设,使得影片中有如此之多的场景,在观众心中永垂不朽。
《假面》使用的是4:3的银幕宽高比
在《假面》中,英格玛·伯格曼同时使用了多种的艺术风格,主要是影像和幻觉之间的关系。他选择了一种与古典电影一致的叙述方式,但是用大胆的视觉叙事颠覆了剧本。
《假面》中的拼接画面
《假面》的电影语法营造气氛,尽可能给叙述增添层次感,随着故事的展开,呈现出一种古怪但引人入胜的分裂感。这部电影探索了灵魂的象征意义,以一种梦幻般的,绝不仅仅是美学的拍摄方式。
影片深入地激发了观众对潜意识的理解,而它斡旋于我们的世界,创造出假面。就像电影中的主角艾玛和伊丽莎白的关系一样,当这两种观念冲突时,观众就知道她们分别代表着外在与内在现实的存在。
一个为我们自己而存在,而另一个是展现给身边的人,因此电影最深刻之处在于它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的答案。
《假面》中的主角艾玛(右)和伊丽莎白(左)
在电影中,我们经常能看见摄影机像个镜子一样观察故事场景,伊丽莎白看向镜头而艾玛移开目光,从穿着、姿态到外貌两个角色如同镜像。
英格玛·伯格曼对艾玛和伊丽莎白使用大特写镜头,使观众面对存在的虚无,持续的让人感到局促的特写镜头,将演员变成身体部分的集合,眼睛、嘴巴、鼻子、头发和毛孔都融合在一起。
伊丽莎白(前)看向镜头而艾玛(后)移开目光
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才是本体?谁才是假面?
大特写下的人类面容展细节展漏无疑
那些符号并不是需要观众去解决和关联的谜题,而是现实的投影,它们将电影放大为一趟哲学的旅程。
《假面》
“福克纳说永远没有绝对正确的故事,我不太乐意谈论何时在干什么之类的事情,因为每次谈到这些都让我很惊讶或沮丧,接受他们采访的时候,你要是告诉他们这部作品所要表达了什么,他们就揪着这个话题谈上半天,你就会慢慢失去了兴致。”——英格玛·伯格曼
英格玛·伯格曼
《假面》的创造性技巧不是反映了英格玛·伯格曼对探求存在这一领域的渴望,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需求,对艺术可能性的沉思。
但如果你一定要解析这部电影的图像意义,也许应该要从电影的两个重要时刻来寻求探索。
《假面》开头
第一个是电影的开头,观众能看到放映机投射出电影和意象的混合物,在此刻电影像入口一样,如同镜子般映射出你的需求。
《假面》通过发问来让我们思考真理,如果没有文化面具的遮蔽,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独立的个体?
电影成为一扇可触及的窗口,让我们一窥虚拟与现实、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关系,但是英格玛·伯格曼并没有让观众困惑恍惚,也没有保持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他用一种幽默方式,也许可以说是大胆的手段,将主角艾玛和伊丽莎白最后的对话放映了两次。
不同机位角度下的对话
另一个重要的时刻,英格玛·伯格曼释放出了感觉、视觉与知觉的基本张力,观众在影像上可以看出该片的关键电影语法,淡淡的脸庞轮廓与黑暗中的剪影相映衬。
《假面》中两位女主角的合成图像片段
角色的心理崩溃,便由这一著名的合成图像呈现出来,两个女性的脸合成一张,这个特殊的场景以及象征意义,也许是整部电影最违背常情的地方,因为它试图通过形而上的影像,来刻画人性的本质。
英格玛·伯格曼在传达主观性能够造成改变力量的同时,挖掘出了多层的含义,他并非致力于制造任何标准答案,而是创造出开放意义的大路,毕竟这是一部电影。
《假面》
《假面》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它在哲学意义、视觉叙事、电影语言方面都有深层次的探讨。
可以用女性主义叙事去解读,电影中女性为了在社会传统下生存,必须戴上面具,成为妻子、母亲;也可以用人的两面性去解读,电影中一面是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而另一面是我们自己本身,但这些角色其实是同一个人。
《假面》
当然,还有一种解读,就是《假面》将电影媒介变成了一把钥匙,打开符号和幻觉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通往潜意识。
不管你如何去解读这部电影,在影片的最后,言语与沉默、现实与电影、假面与本体、演员与灵魂彼此纠缠,又回到那些问题上,什么造就如今的我们?又是什么定义了我们?